白奚:名家學派在稷下學宮的興起
2025-10-23 09:56:48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 作者:白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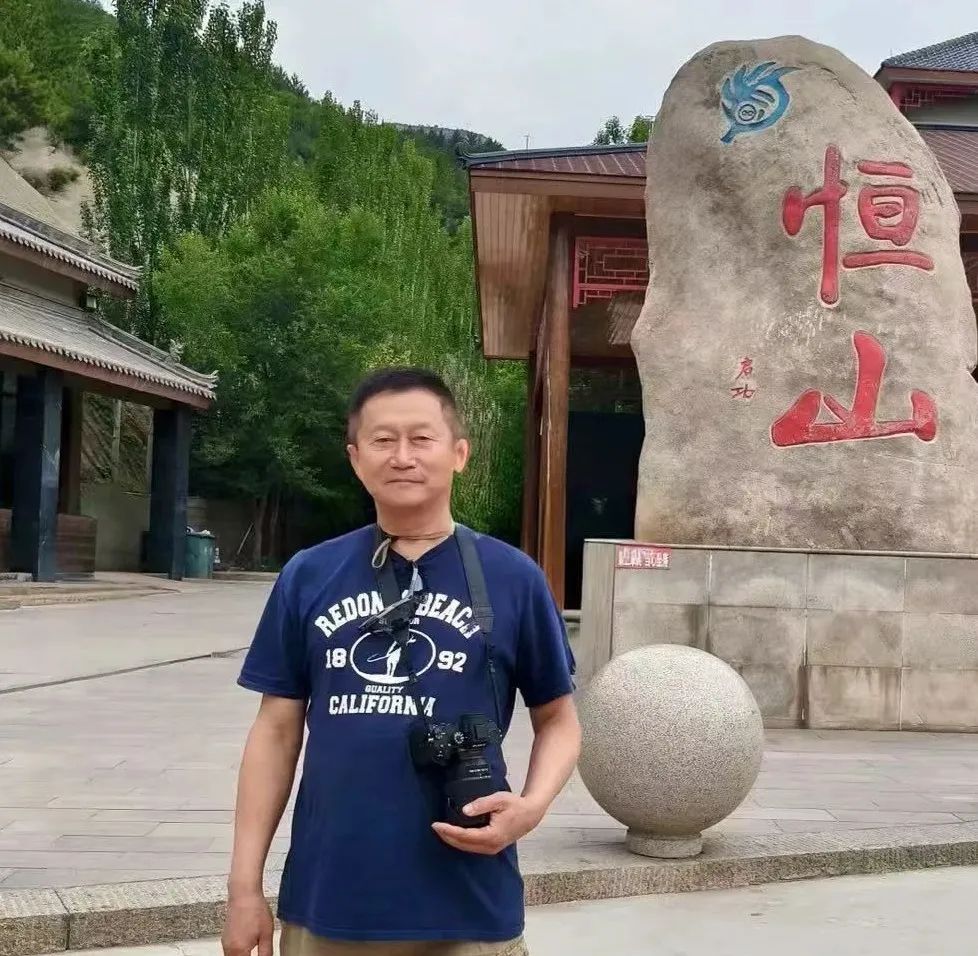
名家學說大體上可以看作古代的邏輯學,是戰國百家爭鳴時期出現的一個極具時代特色的學派,有名辯派和名法派兩個分支。名法派是名家的主流,他們討論的問題以名實關系為主,用來支持以法治國的政治主張。在百家爭鳴的高潮時期,名家有著高光的表現,其中熱衷于論辯術的名辯派人物更是出盡了風頭,名家也迅速達到了學派發展的高峰。齊國的稷下學宮是百家爭鳴的主要場所,也是名家學派的興起之地。
一、關于鄧析其人與《鄧析子》其書
討論名家學派,繞不開鄧析其人和《鄧析子》其書。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鄧析是名家學派的創始人,或曰“早期的名家”。這種說法雖然缺乏論證,大體上只是一種認定,卻被大多數學者習慣性沿用至今。名家作為嚴格意義上的學派究竟出現于何時,是值得進一步深入討論的問題。近年來,對名家的研究雖然有了很大進展,但在名家緣起的問題上依然是一仍舊說,缺乏深入辨析和論證的專題研究。
鄧析是鄭國的大夫,與孔子同時,他擅長法律,經常聚眾講授訴訟的技巧,后被鄭國的執政者以擾亂國政的名義殺害。據《列子·力命》載,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他善于抓法律的漏洞,長于論辯之術,《呂氏春秋·離謂》說他“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荀子·非十二子》也說他“好治怪說,玩奇辭”。從這些記述看,人們對鄧析的評價基本上是負面的,他的思想多是一些模棱兩可、故意混淆是非的內容(“兩可之說”“無窮之辭”),善于用各種奇談怪論和詭辯術來達到爭訟的目的,這同講求嚴謹推理和求真求實的邏輯學的精神和原則相違背。鄧析的行為和風格,同后來戰國百家爭鳴時期的名辯派頗為相似,所以在他去世兩百多年后,其名聲和影響力有所抬升,由此被后世學者視為最早的名家人物和名家學派的創始人。
今本《鄧析子》一書,共有《無厚》和《轉辭》兩篇,大多數學者視其為偽書。該書到底是真是偽,要看我們如何界定偽書。筆者認為,如果必謂其書為鄧析本人所著方為不偽,則其書必是偽書;如果其書只是托名鄧析,內容出于戰國時人之手,則應視為先秦舊籍,不宜判為偽書。筆者認為,《鄧析子》一書屬于后一種情況。本文無意對《鄧析子》進行深入辨析討論,僅擬從常識和常理出發,結合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特點,簡要地對鄧析其人其書及其同名家學派的關系談一些看法,以此支持名家興起于齊國稷下學宮的觀點。
關于鄧析創立了名家學派或者說他是“早期的名家”,有很多疑問難以解釋。鄧析卒于公元前501年,其時孔子剛屆知天命之年,儒家學派是否已創立或尚存爭議,若認定鄧析此時已創立了名家學派恐十分勉強,因為這等于承認名家的出現先于儒家。據《呂氏春秋·離謂》記載:“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可知鄧析聚眾所傳授的不過是如何利用法律的漏洞來打贏官司的技巧,這同我們通常理解的學派、學說差別甚大。鄧析被殺時40多歲,剛到中年,很難相信他已有可以稱得上學派的系統的思想。眾所周知,那個時代尚無私人著書之風氣,即便是《論語》《墨子》這樣的典籍也都是學派創始人的弟子、后學們追記集結而成。鄧析并無弟子傳人,其死又比較突然,他的思想如何能集結成書?就算彼時已有《鄧析子》一書問世,為何后來不見任何被提及的蹤跡,只是到了戰國百家爭鳴時期,其人其說才突然出現?若《鄧析子》不偽,則其成書必早于《論語》《墨子》,為何200年不見蹤跡,甚至也未見與鄧析有相似思想和行為的人物出現?戰國之前的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為何也都不見與名家思想相關的材料?名家作為一個學派在漫長的200年中又是如何傳承下來的呢?即使是撇開《鄧析子》一書的真偽不談,單是說名家作為一個獨立的學派早在孔子之時就已出現,是拿不出任何確鑿證據的。
一般來說,認定一個學派的成立,需要滿足一些必不可少的標準和條件,如創始人、代表著作、核心理念、學說體系、傳承系統、學術群體等。名家亦應如此。若以這些標準衡量,春秋時期的鄧析顯然不具備開創學派的條件。筆者認為,從學派的角度考察古代的學說理論,應注意區分觀念、思想和學派這三個概念。因為任何一種成熟的思想理論都不是突然出現的,都要經歷一個醞釀、積累的過程。通常最先出現的是一些只能稱之為觀念的思想萌芽,經過長期的積累,逐步發展出來可以稱之為思想的理論形態,最后才能形成具有完整理論體系的學派。例如,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淵源都十分古老,在成為學派之前都經歷過觀念萌芽、思想積累的階段,最后才形成了學派。陰陽家也是如此,“陰陽”和“五行”作為萌芽狀態的觀念都出現在西周時期,到了戰國時期逐漸發展出較為豐富的思想理論,直到在戰國晚期才形成學派。我們顯然不能把伯陽父以“陰陽失序”解釋地震和《尚書》里的“威侮五行”說成陰陽五行家的思想,而只能看作陰陽五行學說的思想萌芽。關于仁、愛等道德觀念和禮樂文明的思想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經長期存在,我們顯然不能把這些視為儒家學派的思想,只能看作儒家學派的思想淵源。關于“道”的思想,推崇柔弱、謙下、不爭的生活態度以及欲取姑予、功成身退等思想在老子之前也已存在,我們顯然只能把它們看作道家學派的思想來源,而不應直接看作道家學派的思想。同樣的道理,即使春秋時期的鄧析已經具有了一些可以歸之于后世名家學派的思想觀念,也不宜說他已經創立了名家學派,最多也只能說他是后世名家學派的思想先驅。當然,若要在更早的古人中尋找名家學派的思想先驅,也只有鄧析能沾上一點兒邊了。關于鄧析其人,史書中只有《左傳》記載其被鄭國執政者所殺一事,此后兩百多年沒有被人提及,但是到了戰國時期的《列子》《荀子》《呂氏春秋》等諸子著作中,關于鄧析的事跡和言論卻突然大量出現,難免讓人懷疑這些都是那一時期的學者們由于某種機緣和出于某種需要而偽托。
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學說集中出現。從學派的角度看《鄧析子》的內容,多為戰國道家、法家、名家、雜家、黃老之言。這些內容散發著戰國百家爭鳴時期以法治國的時代氣息,顯然與鄧析所處的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不符。《鄧析子》一書應是稷下百家爭鳴時期某位或某些兼有名家、法家、道家思想的學者假托鄧析之名所作。將鄧析這位久遠的歷史人物認定為名家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同名家學派興盛的歷史情境難以相合。名家作為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極為特殊的原創性學派,關于它的興起,只能用稷下學宮諸子百家爭鳴論辯的時代背景和當時各國變法圖強的政治需求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二、名家之名辯派與稷下學宮
先秦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最為繁榮的時代,這是大家都認可的事實,但是從老子、孔子活動的春秋晚期到戰國中晚期至少有200年的時間,我們仔細考察便可發現,在這個大的時間段內,古代思想文化不是勻速發展的,而是越到后來發展得越快,在戰國中后期達到了高峰。促成這個變化的關鍵因素就是齊國稷下學宮的興辦。在稷下學宮興辦之前,學者們天各一方,往往互不知曉,缺少交流的條件,所以思想文化發展較為緩慢。戰國中期,田齊政權興辦稷下學宮,匯聚了來自列國的大量學者,齊宣王執政時期稷下先生已有“數百千人”。在這里他們可以朝夕相處,頻繁交流,極大地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發展,這樣的局面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稷下學宮的學者們除了著書立說、講學授徒之外,面對面的討論和辯論肯定是少不了的。學者們自信滿滿,認為自己的思想主張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正確的,這樣必然會引發大量的辯論。僅從《孟子》書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淳于髡、告子等人同孟子的辯論,還有孟子對其他學者思想主張的諸多批評,這些辯論都發生在孟子居齊期間,正值稷下學宮鼎盛時期。稷下學宮還定期舉辦“期會”,史載“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也”。“期會”為學者們提供了發表意見和進行辯論的固定場所。可以想象,爭鳴辯論是稷下學宮最為熱鬧的場面,是百家爭鳴最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場景。
要想在辯論中說服別人或戰勝論敵,除了要有高深的學術思想,還須有良好的口才,必須提升論辯的技巧,否則就不能駁倒對方,就不能取得君主們的信任。所以稷下的學者們包括年輕的學子們都很雄辯,常被稱為“辯者”“辯士”“舌辯之士”。他們的口才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練出來的,可以說,稷下學宮就是“辯論訓練館”,就是“口才培訓中心”。對辯術的強烈需求,催生了名辯派。稷下學宮作為百家之學的集中地和百家爭鳴的主要場所,自然就成了名辯派的大本營,成為他們訓練和驗證口才的絕佳之地。這里聚集了大批的“辯者”,他們熱衷于鉆研和錘煉論辯術,總是喜歡選擇一些稀奇古怪的命題進行辯論,這些辯題通常都是些不顧事實的語言文字游戲,與常識相反,與常理相悖,不乏我們今天稱之為詭辯的命題,比如“卵有毛”“郢有天下”“雞三足”“火不熱”“輪不碾地”“犬可以為羊”“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之類。很多人都因為擅長這類辯術而在稷下學宮名噪一時。熱衷于辯術的人在稷下學宮形成了一個顯赫的群體,他們的相關理論也很快形成了一套學說,于是名辯派在稷下學宮的興起便水到渠成了。由此可見,名辯派是在一個并不太長的時間段內出現的,它的興起離不開稷下學宮提供的思想文化條件。
稷下的辯者們不在乎論題是否正確,也不在乎結論是否符合事實,只在乎如何在論辯中駁倒對方,他們一個個巧舌如簧、怪招頻出,能讓對手無言以對的就成為勝者,往往是一戰成名,贏得眾人的追捧。如“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辯論中落敗的一方,只能怪自己嘴笨說不過人家,心里肯定是不服氣的,所以《莊子·天下》說辯者是“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確實是道出了辯者的局限,不過這不正是辯者們苦心追求的效果嗎?
名辯派雖興起于稷下學宮,但其影響力并不限于稷下學宮,著名學者惠施、公孫龍都沒有來過稷下學宮。他們憑借縝密的邏輯思辨和思考問題的深度而在學術思想上大有創獲,有著作傳世,他們的名聲也傳遍列國,成為當時名辯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隨著稷下學宮的衰落,熱衷于辯術的這部分名家人物失去了依存的群體和活動的場所,旋即就遁跡了,此后名辯派也從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中消失了,再也沒有出現。名辯派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卻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史記·太史公自序》評價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批評的正是名家中的名辯派。“苛察”形容名辯派對事物的觀察和辨析過于細微煩瑣,“繳繞”指的是名辯家的詭辯饒舌。“儉”有“查”義,引申為明察,這原本是名家的專長和優勢,可惜他們鉆進了“名”的牛角尖,僵化地“專決于名”,以至于背離了事物的本真和人情常理。《漢書·藝文志》評價名家“及譥者為之,則茍鉤鈲析亂而已”,顏師古注引晉灼曰:“譥,訐也”,在對話和辯論中攻擊對方的短處和理論漏洞,這正是辯者慣用的論戰手法,可見班固批評的“譥者”即指名家中的名辯派。名辯派的觀察不可謂不細,辨析不可謂不察,但可惜過于拘執于“名”,反而把本來清楚明白的事情搞亂了。《隋書·經籍志》評價名家曰:“拘者為之,則苛察繳繞,滯于析辭而失大體”,也是批評辯者拘執于概念分析而背離了常識常理。《荀子·非十二子》也批評辯者“好治怪說,玩奇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怪說”“奇辭”指的就是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類的論辯。荀子認為這些辯題雖然精細明察,但是對治理國家沒有用處,應該被制止。
名辯派的理論雖然如荀子所批評的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但也有其獨特的思想價值。中國古代的各種學說理論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現實的社會問題特別是政治問題格外關注。他們的學說是以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為主要內容,大概只有名辯派是個例外,基本不涉及社會政治問題。名辯派的思想內容包含著純粹的語言學、認識論和邏輯理論,這對于民族文化的傳承、發展和提升是不可缺少的。中國古代的名家在稷下學宮時期達到了發展的最高峰,可惜后繼無人,沒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長期存在,也沒能很好地融入以儒家和道家為主體的古代學術體系中,這對于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名辯派的理論涉及的內容極為廣泛,從宇宙萬物的起源、科學道理到邏輯理論、辯證思維和相對主義哲學,可謂無所不包。其中雖有大量詭辯術的內容,但也不失其積極的思想意義和理論價值。名辯派大多是高智商的佼佼者,他們的思想中蘊藏著先哲們的智慧和思維精華,不可簡單地被視為詭辯或文字游戲。
三、名家之名法派與稷下學宮
名辯派雖然逞口舌之辯而受人追捧,但往往因遠離現實社會的實際而招致批評。前引齊辯士田巴“議稷下……一日服千人”,可謂一時風頭無兩。但他受到了12歲少年魯仲連的詰難,被批評只是空談,玩弄概念游戲,不能解決任何現實問題。對此,田巴難以反駁,于是“終身不談”。足見名辯派誠如荀子所批評的“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難以被社會主流接納。真正成為名家之正宗和主流的是名家學派中的名法派。
名法派的特點是將名家的邏輯理論應用于現實政治,為當時的主流政治主張——法治做論證和理論指導。這一派名家也是興起于稷下學宮。他們雖然沒有名辯派那么熱鬧和出風頭,但以其獨具特色的名實理論和注重嚴密論證的邏輯思辨而流行于稷下時期,并作為一種公共的思想資源滲透于稷下諸子百家的學說,提升了各學派的理論水平,為列國的社會治理和法治實踐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近年來,學界比較重視對名家不同流派的區分,如曹峰認為有兩種不同的名家:“一種是倫理學政治學意義上的;一種是語言學邏輯學意義上的。或者說一種是‘政論型的名家’;一種是‘知識型的名家’。”高華平也認為:“用現代的學術概念來說,先秦學術思想中的所謂‘名’之二義,乃分屬于政治、倫理或禮法之‘名’和‘名學’或邏輯學之‘名’。”所謂知識型名家或邏輯學之名家即本文所謂“名辯派”,政論型名家或政治、倫理之名家與“名法派”相對應。
名法派亦稱形名家,興起于戰國列強爭雄時期。當時席卷列國的變法實踐亟須獲得理論支持,名家就提供了這樣的理論支持,其名實理論和邏輯辨析可以為法治提供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論指導,這樣的理論需要就催生了名法派。名法派的理論以論證和維護法治秩序為目標,亦稱為形名法術派、形名家、刑名家。該學派的某些人物在歷史上常被歸為法家,可見形名家和法家的理論聯系之密切。
形名家的理論淵源可以上溯到孔子。孔子的“正名”作為古代政治理論的基本原則,歷代學者無不奉為圭臬。戰國百家爭鳴時期興起的名法派把“正名”作為其政治主張的核心內容,《史記·太史公自序》點評名家曰:“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又曰:“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漢書·藝文志》也說:“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可見,正名的主張是名法派的宗旨,是該學派理論的合理性和正面價值之所在。
名法派在正名的理論框架下發展出一套旨在確保名實相符的具體操作方法,用來驗證理論和決策是否正確和考核官員是否稱職,此即《史記》所說的“正名實”“控名責實,參伍不失”,亦即所謂的“形名”術。這樣就把原本只是基本原則的“正名”落實為一些可以實際操作的具體方法。此種理論在戰國時期極為流行,儒家、法家、黃老道家等學派都接受了這一理論并對之進行豐富和推進。
馬王堆漢墓帛書《黃帝四經》是當下多數學者認同的戰國黃老道家的奠基之作,其中有迄今所見最早的形名理論,為其后形名理論的傳承發展定下了基調。帛書《黃帝四經》的形名理論有一個極重要的開創,那就是以名論法,在名和法之間建立了密切的理論聯系。法治是戰國時期列國政治舞臺的主旋律,法治實踐要向縱深展開,建立法治下的新秩序,法家學說本身也需要理論提升,在這方面給予最多支持的是道家和名家的學說,而帛書《黃帝四經》在這兩方面都有開創之功。以“道”論為核心的道家哲理為法治提供了形上的論證和指導,從宇宙論和本體論的高度為法治的合理性、必要性、權威性、公正性等提供了論證和指導,從而極大地提升了法治思想的理論高度。名家對法治的支持則比較具體和富有操作性,其形名理論以邏輯和辨析的方式為法治的制定和實施提供指導,從而極大地加強了法治的有效性和嚴謹性。可見,道家和名家的引入,極大地提升了法治學說的理論水平,推動了法治的社會實踐,帛書《黃帝四經》在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在《黃帝四經》中,道、法、名三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黃帝四經》的第一句話就提出“道生法”的著名命題。這個命題首次把道和法結合了起來,確認了法是根據道的原則制定的,這就從宇宙論和本體論的高度為法治找到了理論根據,也為道家哲學向社會政治領域的拓展和應用開辟了廣闊的空間,“道生法”堪稱黃老道家的第一命題,為此后的黃老道家的發展確定了基本方向。在《黃帝四經》中,名與法結合緊密,名賦予法合理性,法是正名的工具;名為目的,法為手段;名為裁決者,法為執行者。“名”與“道”的引入,使得戰國時期的法治實踐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論支撐,此兩項皆為《黃帝四經》首創,可謂功莫大焉。
限于篇幅,本文僅以尹文和《尹文子》為例探討名法派的主要思想。尹文,齊人,齊宣王時期著名稷下先生,名家名法派的代表人物,所著《尹文子》是名法派最重要的著作。今存《尹文子》共有《大道上》和《大道下》兩篇,應是先秦已有的古籍,然而其真偽仍存在很大的爭議。尹文的學派歸屬說法不一,有人把他歸入道家,因為他的著作就以“大道”為篇名,書中第一句話就是“大道無形,稱器有名”,而且書中也確實多次稱引《老子》,講述和運用道家的理論。也有人把他歸入名家,因為他書中的主要內容都是講“名”的,圍繞“名”展開的理論是古代的邏輯學,他本人也以擅長邏輯辨析推論而著稱。漢代學者不僅把他歸入名家,而且多次提到尹文先于公孫龍,公孫龍曾經稱引他的思想,公孫龍是名家學派的著名代表,這說明尹文的學說和名家更為相近,把他歸入名家更能突出他的思想特色。尹文思想的理論取向,在于他把名家的邏輯學理論同當時變法圖強、治國理政的實際需要結合起來。他在政治上主張法治,名法結合、以名論法是他的專長。
尹文是名法派最重要的理論家,提出了名實互定、形名互檢的思想,使原來名與實的單向關系變成了雙向關系,這是他對形名理論的重要貢獻。《尹文子·大道上》曰:“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在這段話中,“名以檢形”和“形以定名”兩個命題構成了“名”與“形”之間的第一個循環:“名”(規則)是根據“形”(現實)確定的,是對“形”(現實)的確認,這一經過確認的、既定的“名”就可以作為檢驗“形”(現實)是否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標準,與“名”相符合者即合理、合法,不符合者即非理、非法。但是,社會是不斷發展的,現實是不斷變化的,作為規則的“名”也不能一成不變,否則就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因而,變化了的現實——“事”(“形”)——又可以作為檢驗“名”(規則)是否過時、是否仍然適用的標準。此時如果出現了“名”與“事”不符的情況,需要改變的就是“名”而不是“事”,就要對“名”進行修正,使之與業已被證明是合理的“事”相符合,如此經過修正的、與時俱進的“名”才可以作為新的標準用來檢驗和規范現實的社會關系。這就是尹文所謂“名以定事,事以檢名”,這兩個命題就構成了“名”與“形”之間的第二個循環。尹文所設計和論證的“名”與“形”之間的這兩個循環是首尾相接的,如此就使得名實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單向的、一成不變的,而是雙向的、動態的,這是對形名理論的一個重要發展,其中包含著理論必須適應變化了的新現實的思想。
“尋名以檢其差”即依據名的要求來檢驗事實是否與之相符,找出不相符的現象并予以糾正,這正是形名理論的核心訴求。帛書《黃帝四經·經法》的“循名究理”,《管子》的“修名而督實”,《韓非子·定法》的“循名而責實”,《文子·上仁》的“循名責實”,《荀子·正名》的“制名以指實”,都是在重申這一核心訴求。
“定分”是形名理論的另一重要內容,“分”即“名分”。尹文認為:“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人的本性是自私好利的,不能沒有爭奪之心,但社會并沒有因此陷于混亂,這是由于“名分”對人的私欲起到了限制作用。他舉彭蒙之言為例:“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尹文認為,名分是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得力工具,一個大家都認可和恪守自己名分的社會就是一個治理良好的社會。他說:“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士,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足見“正名”和“定分”對社會的穩定有序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是多么重要。
尹文提出“名以檢形”和“名以定事”,要求用“名”來規范和檢驗現實,并要求對不符合“名”的現象予以糾正。那么用什么來糾正呢?尹文的回答是用“法”。因為“名”本身并不具有強制性,只是告訴人們離開了法的強力支持、維護和保障,正名定分的主張就只能流于空談。所以尹文經常把名和法結合起來加以論述,他主張“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名稽虛實”就是查驗“實”是否與“名”相符,相符則為實,不符則為虛,這是第一步。接下來是“以法定治亂”,即用強制性的法令來維護或恢復“名”所要求的社會秩序。“名”和“法”在尹文的學說里緊密結合,名行于前,法隨于后,名為法開路,法為名護航,他稱之為“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
尹文的學說注重概念的準確性、邏輯的嚴密性和推理的合理性,他用形名理論為法治張目。雖然這一主張在當時頗具普遍性,但唯有他的思想體系最為系統完備,不僅具有代表性,更在理論建構上達到了同時代學者難以企及的深度。在形名理論的支持下,以法治國的理論和實踐得到了明顯的加強和提升,我們只需將早期法家著作《商君書》和晚期法家著作《韓非子》加以對照,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兩者的差異和變化。
(作者系山東理工大學特聘教授,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編輯:董麗娜】
文章、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白奚:名家學派在稷下學宮的興起
- 深入推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充分發揮文化養心志、育情操重要作用
- 尼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聯合研究生院齊文化和稷下學專題研修活動在山東淄博舉行
- 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向曲阜師范大學捐贈傳統文化書籍
- “科圣”之光,萬里同照
- 科學把握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內在邏輯
- Remnants of Suyukou kiln in Yinchuan, China's Ningxia
- 全國政協委員唐旭東:繪就中醫藥發展新圖景
- 從偷偷學藝到非遺大師,濟南“守藝人”的糖人人生
- 文化節慶里的齊魯氣象:文化節,節節高
- 白奚:名家學派在稷下學宮的興起
- 白奚:名家學派在稷下學宮的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