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人文精神
2017-02-15 13:57:00 作者:杜維明 來源:東山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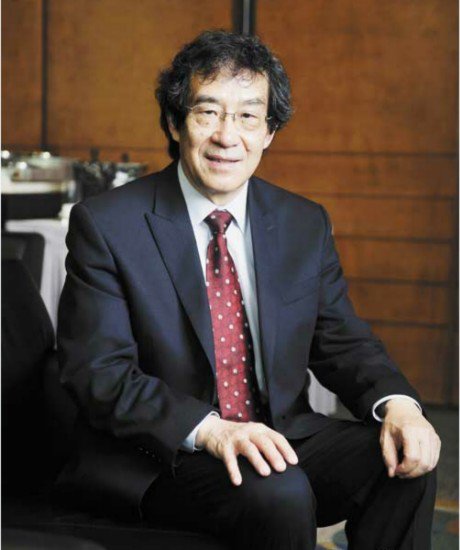
杜維明
杜維明,男,1940年生于中國昆明,祖籍廣東南海。中國當代著名學者,現代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當代研究和傳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國際哲學學會名譽院士(代表中國),中華文化促進會學術咨詢委員 。
杜維明15歲起便研習儒家文化,曾師從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1961年畢業于臺灣東海大學中文系,翌年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前往美國深造,1968年獲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曾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1981年始任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教授,并曾任該校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1996-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長,2008、2013年分別當選國際哲學會聯會(FISP)執行委員、國際哲學學院(IIP)院士。2010年起,任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
在各個時期,杜維明的思想和著述重點有所不同。1966-1978年,著重詮釋儒家傳統,確立了對儒家精神價值作長期探索的為學方向;1978年至80年代末,關懷重心是闡發儒家傳統的內在體驗和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20世紀90年代迄今,所關注并拓展的領域有“文化中國”、“文明對話”、“啟蒙反思”、“世界倫理”等。

一、讀《孟子》之“自得”
陸象山這位歷史上很重要的儒家學者曾經說過,我一生的學問是“讀《孟子》而自得之”。就是說他一輩子的知識都是在讀了《孟子》之后領悟到的。這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他讀了《孟子》這本書,另一方面是他覺得“自得”。現在我們都提倡通識教育,但同時我們也有一個共識,也就是這一生中,無論我們從事的是化學、物理、機械、企業管理、文史哲中的哪一行,如果自始至終沒有和一本重要的經典交過朋友,那么這無疑是非常可惜的。假如我們一生和一本書(這本書最好是經典但不一定是經典,也許是很重要的書)能夠真正交上朋友并成為知音,這對我們的一生意義將是非常大的。我們都知道,日常生活中能交一個朋友著實是非常不容易的。剛開始的時候只能說他是誰,可能在一群人中間能夠把他識別出來;經過一段時間的交談之后,我們才能說認識了這個人,但這還只是泛泛之交,要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也許要一起共事五年十年,才能說和他比較熟悉;但是熟悉也并不表示對他真正有所了解,可能要把他的背景都了解清楚了,才能說對他有比較深刻、比較全面的認識,不過即使到了這個程度,還不能說這個人是真心朋友,真心朋友之間一定是要對話的,好朋友之間知無不言。人生難得一知己,如果這個所謂的知己朋友并不愿意坦誠自己、不愿意對人開放胸懷,這樣也很難和他成為知音。
那么我們怎樣才能使得一本經典,例如《孟子》這本書,對我們開放胸懷,進而和我們成為知己好友呢?要讀《孟子》,首先要有一些古代漢語方面的基本常識,我們也可以借助一些白話文的翻譯(例如楊伯峻的《孟子譯注》)進入《孟子》的精神世界。陸象山還告訴我們在讀《孟子》時要"先立乎其大者",也就是要先把最大的東西建立起來。《孟子》書中有"大體" 和"小體"兩個方面。在孟子眼里,人與禽獸的區別是很小的。他了解到一個人的情欲,一個人的食色,一個人基本的經濟的要求、生存的要求、生理的要求,所有的這些要求在很多地方跟貓或者狗以及很多禽獸都是一樣的,這就是孟子說的"人之小體"。人和動物之間有很多不同,例如人可以用工具,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社會動物,那《孟子》所謂的"大體"是不是就是這些呢?我并不是特別贊同這樣的理解。我繼續追問,這種"大體"可否是一種潛能,它可能永遠不會發揮出來,或者也可以說就是一種傾向,而這種傾向是不是受到外面的影響或是其他地方的影響?假使我們有這種傾向,那它是不是一種真實?我們每個人都有種非常真實內在的而且不時就可以顯現的(潛能),這種叫做“大體”。再看《孟子》的思想,確實有這一面。每人都是小體、每個人都是動物,這是不可置疑的、不必論證的。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使人和其他禽獸有所分別的東西,這并不是我們一般所能在西方哲學里從理性、從工具、從語言的運用來理解的。這樣說來,這個"大體"是不是一個精英主義呢?僅僅是極少數君子、士或賢、圣這些人有,而我們一般人就從來都沒有、也沒有想過的,是一種永遠沒辦法企及的、沒辦法達到的理想人格才是所謂的"大體"嗎?后來我又想到,《孟子》里面有一段話,他說"大體"這種境界沒有一個人可以達到那么高的水平的。"可欲之謂善",它是從善開始的,善的本身就非常難達到;然后下一步就是"有諸己為信",信仰的心——你內部除了好以外還有一些內部的資源,內部的真誠,這才叫做信;而充實謂之美,內部的充實才叫作美;然后不僅充實,而且充實還有光輝,發揚光輝這才叫做“大”;而且不僅"大",還"大而化之"——有兩個意思,一個就是自己能夠“化”,另一個就是能夠轉化,這個才叫做“圣”;那么"圣而不可自知"才叫作神。又從善到信到美到大到圣到神,這對于我們每個人講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太理想化了,太難達到了。如果"大體"是這種,我們絕大多數人一般是沒法體現的。后來陸象山在解讀《孟子》的時候,又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先立乎其大者"的意思就是“志”。我們一般講"有志者,事竟成",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志向和我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中間有一個距離,而這個距離是很漫長的,有些是沒辦法達到的。但在《孟子》思想里面他有一個觀點值得我們考慮:你的志決定你所要的。這個志是什么呢?這個志不是一種知識,它本身就是一種轉化的能力,只要有志就一定能夠得到。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志一定會得到它必要的結果?如果一個人決定了要做基督徒,他愿意做基督徒,這個意愿的本身就使他成為基督徒:我要做佛門子弟,那我決定了要做佛門子弟,我就可以出家做佛門子弟。我決定我要做佛門子弟,也許我有其他的條件,我會改變我的意愿,但是我決定的本身,既是必要的條件也是充分的條件,是可以完成的。《孟子》講的“志”一定還必須包含著結果,因為它所了解的志是一種轉化的能力。所以這樣看來就有兩種可能看起來不太一樣但又有關系的知識,一種就是我們在大學里面所要追求的知識,所有這些知識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知識,我們都要通過一個程序、一個階段來獲得:另外還有一種知識,用現代漢語講就是“會”——我會騎自行車、我會彈鋼琴,在英語里面就是"to know what",知道什么,還有就是"and to know how",知道如何做——一般我們的理解是一種內化的技能,比如說我學騎自行車車然后我學會了,這是我內化的一-種技能,這和我知道所有的自行車的所有各種不同的復雜的機械原理沒有太大的關系——即我沒有真正地學,我一上自行車我就倒了。那這種志向的決定如果算是一種知識,那它是哪一種知識?它是不是就是一種內在的技術?這里就牽涉到"大體"、"小體"中一個很特殊的問題,就是"大體"可以通過我個人主動自覺而發展,這不是精英主義,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做到,每一個個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作了這個決定他就有轉化的可能。但是一般的我們都"一曝十寒" ——我今天有這個決定,但是過十天我就沒有這個決定,我個人也是這樣——常常說是有很強的意愿,然后這個意愿就淡了。但是只要有這個意愿,它本身是絕對可能的,這個也許就是孟子之所以對人那么樂觀、積極的原因。
二、孟子的“性善論”
孟子認為,我們的心有一些東西,不是說我們的心本來就是一張白紙,通過外在的訓練這個白紙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彩色。孟子所謂的心,它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豐富是因為孟子認為心里面有一些只要是人就會有的東西,這就是“性善說”。第一,他相信每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人都非常特殊:一個人有不同的性別,有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年齡段,有不同的地域環境,也有各種不同的社會環境——社會有各種壓力,如果社會非常好的話大家就變得懶惰,如果社會非常不好的話大家就容易變得暴力、有一種憤憤不平之氣,在各種不同的環境里對人有各種不同的負面的壓力。孟子既然知道人有很多不同,整個社會有那么多的力量,有的人沒有辦法充分發揮他的潛力成為"善、信、美、大、圣、神"的人,而在戰國是很暴力的時代,他是不是就是因為樂觀、因為理想主義給我們打氣,還是因為他有另外一個很深刻的看法?我想他是有另外一個很深刻的看法,他認為人性是從天上來的。因為從郭店出士的文物我們了解到性本身不是一個原則,不只是一個理由,也不只是使我們人逐漸完成我們人格的基礎,性的本身是有創造力的。我們每個人的人性它本身有創造力,它本身是有動力、是向上發展的(不是說它有向上之機理),它不是一個靜態的結構,它能夠發展、能夠動,就是通過心,儒家的“心性”是從這個角度提出來的。那這個“心”有一些什么特性呢?很簡單地說,這個心是可以“感”的,是有情的,能夠感動,如果不能感就不是心。所以孟子講"惻隱",我們一般講的惻隱是同情,但有些人說同情也是后天培養的,不是先天有的。但是孟子這講的是更根本的,就是因為里面所謂的“feeling”就是我作為一個人我能夠“感”,我受到外面的力量我能有所感覺,除非麻木不仁的人——麻木不仁就是批評一個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整個感覺都完全沒有了,這個人就死亡了,所以說"哀莫大于心死"。另外每個人都有意志,都可以做一個決斷,這不是外面加的。如果一個人決定要做某種事情,他決定的這個事情的本身一定導引了他做這個事情的結果,我要改善我自己,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力量,這個本身就可以轉化。孟子講了“四端”,所謂“仁、義、禮、智”,不是外面加進來的一種價值,而是每一個人都有的、能對外面的事物有所感。當然你如何做、是對還是錯都要經過一定的訓練。你能夠感覺到感情的力量是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看到一個小孩掉到井里面,并不是說你要去救他或者是要做什么,但是我們在心里面會有一種震撼,從孟子講起來就是助緣、就是一個力量,而這些力量就是人之所以成為人所帶來的,是從天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