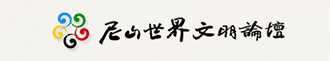孫廣:經學須由文學而顯 ——作為中國古典學基本方法的文章學
2025-10-07 15:26:55 作者:孫廣
自2024年以來,隨著中國古典學學科的設立,學界對這一學科的概念范疇、價值意義等,作了非常周備的論述。然而,對于中國古典學的研究方法,似乎少有論及。歸根結底,中國古典學的核心是中國古代經典,如何讀懂中國古代經典,便是中國古典學的基本方法。只有在讀懂中國古代經典的前提之下,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能談進一步的傳承轉化、開拓創新。
隱于理論與方法背后的經典
經典解讀的主體對象是經典本身,但很可惜的是,在當前中國古典學的研究中,理論和方法已經成為研究的主體,而經典本身,在多數時候只是各種理論和方法的“試驗田”,淪為了材料范圍。
首先是理論的遮蔽。自晚唐“疑經”思潮興起,個人的思想創造便成為絕大多數學者的追求,并催生了宋明理學這一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學術思想。從中國思想史上來看,宋明理學實在是一座高峰,朱熹、王陽明等人的思想尤可謂博大精深。因此采用理學、心學、氣學的理論以解讀經典,遂成為宋明時期的普遍做法。晚清民國以來,西方學術思想傳入中國,迅速取代經學和儒學,占據了學術思想的高地。于是采用西方學術思想來解讀中國古代經典,又成為百余年的學術主流。而且,隨著西方學術思想的發展變化,以及中國思想界對西方認識的不斷加深,我們對西方的各種學派、思想、理論的接受與傳播不斷更新,對于中國古代經典的解讀,尤可謂眾說紛紜。從經典解讀的角度來說,這些理論也在某些方面深化了我們對經典的認識。例如程朱的“天理”、王陽明的“良知”、康德的“道德律”,都為解讀孔孟之“仁”提供了不同維度的重要參照。但相比而言,這些理論帶來更多的是“理障”,使得經典淪為這些理論的論證材料,而經典本身反而遭到了遮蔽。例如宋明學者基本都是站在“理氣論”的立場來談孟子,于是孟子“性善論”只是“論性不論氣”的“不備”之說。又如部分研究墨家名學的論文,雖然使用了《墨子》的文本材料,但展示的卻是西方邏輯學理論。凡此之類,皆是將古今中西的各種理論作為目的,而不是以經典本身為目的。
其次是方法的遮蔽。清儒提倡考據,本是為了解讀經典,還原經典的“本來面貌”。然而,隨著考據學的發展,文字、音韻、訓詁等考據方法日益專業,形成了類似于“方法論”這樣的理論自覺。如高郵二王,就已經形成了初步的“語法學”理念,并用于經典考證。其后如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古史辨派的“層累說”,以及西方的邏輯學、語言學、階級分析法等等,都深刻影響了我們對中國古代經典的解讀,深化了我們對經典著作的認識。但是,在近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似乎越來越強調“方法論”的重要性,而經典本身反而不再受到重視。體現在研究成果上,便是經典淪為方法的應用場。例如部分研究語言學的學者,利用結構語言學的方法去解讀古代經典,只注重“文例”而不注重“語境”,導致許多解讀都無法在具體的文本中講通。又如部分研究出土文獻的學者,依據某個出土文獻的個別例證,甚至只是個別字的特殊寫法,便對經典的某個說法提出了顛覆性的解讀,導致與經典的整體特征相違背。再比如部分研究訓詁學的學者,為了達成某個新的解讀,在面對經典文字時,由甲而乙,經乙至丙,轉相訓詁,無所底止,以至于一字之訓,可通萬物,尤可謂穿鑿附會。凡此之類,皆是將研究方法作為主體,而經典本身最終淪為了一種應用的場地,而非研究目的。
注經傳統及其回歸
理論與方法對經典的遮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以解經為目的,使得經典喪失了主體性。因此,要對這種研究現狀予以糾偏,就必須以經典解讀為本位,回歸我國固有的注經傳統。
我國的注經傳統發源于戰國,成形于漢代,并一直傳承到清末民國時期。漢代“五經博士”制度取代此前“備顧問”的博士制度,便標志著以經典及其解讀為本位的學術范式正式確立。此后博士家法師承傳續,至東漢末發展為以馬融、鄭玄為代表的“義疏學”,直至唐代《五經正義》,成為注經傳統上的一座高峰。宋代以后,雖然學者們深處“疑經思潮”之中,對經典及其注解頗多不滿,但也創作了大量的注經著作。甚至一些極為宏大的思想創造,也必須通過注經的方式予以呈現,如程朱對《周易》、《詩經》、“四書”等經典的注解即是。明代學者如王陽明等雖然不尚注經,但更多的學者依然創作了大量的注經著作,如焦竑、王夫之等即其典型。至于清代,考據之學大興,注經著作的質量與數量都居于歷代之冠。今學界所通用的經典解讀著作,如“清人十三經注疏”和“新編諸子集成”,便絕大多數都是清人作品。由此可見,自漢至清,注解經典,一直是我國學術研究的基本范式和根本傳統。
自漢代設立“五經博士”,一直到清末的科舉考試,學界一直有著“專經”學習和研究的傳統,成為學者的前提就是“明經”,至少“五經”必通其一。在這樣的制度支撐下,注經傳統得以發展壯大,不斷傳承。然而,近代以來,學術分科成為核心體制,并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而日益精細、日益嚴苛,形成了牢固的學科壁壘。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具備各種專項能力的學科人才成為研究主力,而傳統的“明經”人才則不斷凋零。因此,晚清民國以來,注經傳統便逐漸式微,學術研究呈現為理論、方法、歷史三分的局面,并各自往深廣方向發展。雖然如程樹德、程俊英、楊樹達、楊伯峻等部分學者還有高質量的注經著作,使得注經傳統不絕如縷,但更多的學者對注經的貢獻,只在于對經典中的個別問題作較為深入的研究,并不關注某部經典的完整解讀。當今市面上仍在不斷出版各類經典注解、譯注類著作,大多也都是剽剝清儒,只在部分問題上補苴罅漏。整體來說,學界隱隱呈現出一種“經自清儒以后不必再注”的態勢。
所幸的是,近年來,注經傳統已經有逐漸回歸的趨勢,而超越清儒的注經著作,也已經出現了苗頭。如楊逢彬的《論語新注新譯》《孟子新注新譯》主體仍然是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鄧秉元的《孟子章句講疏》《周易義疏》則主要采用哲學范式,雖然還呈現出鮮明的學科特性,但在解經方面取得的成績已足以引人注目。而如程水金《尚書釋讀》《莊子釋讀》,以及楊海文“《孟子》單章研究”的幾篇論文,則已經展現出超越學科界限的特點,能夠將考據、義理、辭章融為一體。隨著中國古典學學科的建設,未來或許會在人才培養體系中出現“明經”教育——這在許多“國學班”的培養體系中已經得到了長期的實踐,也一定能培養更多的“明經”學者,推動注經傳統重新走向繁榮。
作為解經方法的文章學
回歸注經傳統,必須以經典本身為本位,否則仍難以避免理論和方法的遮蔽,如郭象注《莊子》、朱熹注《四書》即是如此。對于傳統解經方法,姚鼐“考據、義理、辭章”三分的說法可以信從,而三者也都不可或缺。但相比而言,考據和義理對于經典文本來說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清儒重考據,必強調文字音韻學的基礎性意義,而其后終不免蔽于考據方法,沉溺于單文只字,徒為尋行數墨之學。民國以來重義理,必強調思想學說的價值意義,而其后終不免蔽于理論學說,甚至于斷章取義,強古人以就己說。然對于辭章來說,就無法脫離經典文本而獨立存在。因此,今欲凸顯經典本身的主體性,必須以文章學為核心。
作為一種解經方法,文章學的核心就是立足經典文本,以文本脈絡和語境為核心,確保各種考據成果或義理闡發服從于經典本身,為經典解讀提供支撐。在這樣的解經活動中,所有的理論、方法,只有在契合經典本身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采納,否則便在排除之列。這一解經方法源于章句之學,其后在歷代注經活動中均有體現,而明清學者的經書和諸子評點、桐城派的文學解經理論,亦對此有所貢獻。這是我國固有的解經傳統,也是回歸經典的必經之路。
章句學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出土文獻中的章句符號,以及類似《詩經》中“《關雎》五章,章四句”的劃分,最初只是單純地劃分經典的文本層次。隨著解讀需要,學者開始在章句之中添加各種注釋,早期如漢代律章句中所附的簡短說明,后則逐漸擴展增益,形成了包括訓詁注釋、史事引證、章旨概括在內的成熟的章句之學,如趙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辭章句》即其代表。章句學的核心就是“分章析句”,即分析、梳理經典內在的文本層次和邏輯結構,此即文章學的分析。其間具體的考證,則是用以證成和支撐這些文章學分析的基礎。而更進一步的義理發揮,則是建立在正確疏通經典文本的基礎之上。簡而言之,章句學是以考據為基礎,以義理為曼衍,而經典的文本則是聯結二者的中心。而另一方面,相應的考據是否準確,義理發揮是否得當,也必須回歸到經典文本中予以驗證。
由于辯難、師法、官學等多種原因,作為解經之法的章句學逐漸變得繁瑣、僵化,章句這一解經文體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以經典內在的文本層次和邏輯結構為突破口的解經方法,仍然體現在歷代的注經著作之中,成為一種常用的解經方式。例如朱熹《孟子集注》云:“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這就是對經典上下文文本層次的分析。時至今日,這樣的方法運用也常見于各類經典解讀著作之中。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由于缺乏基本的理論自覺,這樣的章句分析并未得到特別的重視,在深入考據或發揮義理時,便往往會遭到遮蔽甚至割裂。
明清時期,原本用于文學作品的評點之法,被運用到了經學和諸子學領域,形成了一個文章學與經典互動的風潮。具體到解經方面來說,如李贄《四書評》評點《孟子》“盡心知性”章云:“首節先說‘心’‘性’‘天’是一個,不是三個,下面便教人下手,故有兩‘所以’字。”他通過“所以”這一關鍵詞,劃分了此章的文本層次和邏輯結構,而由此體現的本體論與工夫論界限,也就十分清晰了。然而,由于明清時期的經書和諸子評點,其根本目的是總結經典所體現的文法,在文學創作上“宗經”,因而相關評語多是賞析性質的“妙”“奇”,或文法方面的“頓挫”“開合”等內容。相關著作對于經典解讀雖有所涉及,但并不重視,因此終究只是文學評點,而不是經解。
清代桐城派興起,乃于文學解經方面有了理論上的突破。陳用光曾說:“諸經雖不可以文論,然固文也。不知文、不能文者,則不可以通經。”明確指出需要以文章學來達成“通經”的目的。到了晚清,吳汝綸更是提出:“士生三代后,而欲求古人精微之所寄,舍文章之學,其誰與歸?”強調文章學是解經的唯一途徑,真正從理論上確認了文章學在解經方面的獨到價值。然而,可惜的是,桐城諸子的主要成就還是在于文學方面,在解經方面缺乏有價值的代表性著作。即便是晚清桐城派的吳汝綸、馬其昶、唐文治等,雖然著有解經作品,也未能彰顯其文章學解經的方法。他們的文學解經理論雖好,卻并未得到很好的實踐。而后隨著“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批判,以及西方思想和方法的涌入,桐城派這一文學解經的方法,也就逐漸被時代遺忘了。
近年來,明確采用文章學解經的代表是程水金教授。他指出:“經學須由文學而顯,舍文學亦無經學。不通文章之道,經學必晦而不章。”這一說法,可謂桐城諸子之同調。而在他的《尚書釋讀》和《莊子釋讀》中,這種解經方法已經得到了具體的實踐,取得了不俗的解經成效。
由此可見,文章學是自漢代以至當代都傳承不絕的基本解經方法,且相比于傳統的考據或義理兩端,更能凸顯經典本身的主體性。可惜的是,自漢代章句學式微之后,這種方法便主要成為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領域的專有名詞,雖發展出了豐富多彩的理論和方法,卻幾乎未再轉入解經活動中來。時至今日,我們有必要將其重新納入解經活動之中,從而凸顯經典本身的主體性,真正做到讀懂經典。同時,我國古代的文章學理論,也不再只是紙面上的研究對象,而是作為中國古典學的基本方法,活在我們當下的解經活動之中。
結語
采用文章學解經是為了突出經典的主體性,從而真正讀懂經典。但是,追求讀懂經典并非一種“原教旨主義”,而是跳出歷史的遮蔽,體認真正的中華文化根脈,從而為當代的文化建設、文明互鑒提供基本的參照系。正如程水金教授所說,我們既不要“照著講”,也不要“接著講”,而是要回歸元典“重新講”。唯其如此,我們方能真正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而這,也正是中國古典學的根本追求。
(作者:孫 廣,系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
【編輯:】
文章、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